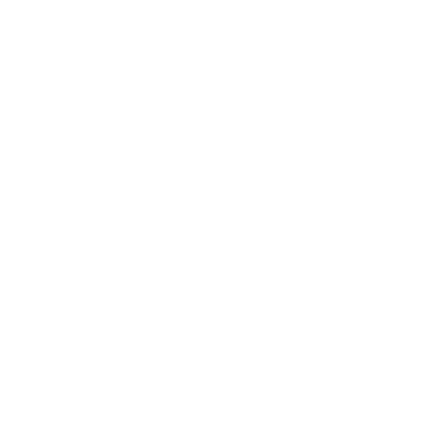|
前一天,在一个路口看到有个爆米花摊点,忍不住放慢了脚步,随着“砰”的一声,爆米花的香味弥漫开来,也启开了我的记忆闸门。 小时候,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,静谧悠闲的乡村里,常有爆米花的手艺人走村串巷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里孩子谈不上吃零食,能吃上一把爆米花,就算解馋了。那香香甜甜的爆米花,让我的童年增添了几多乐趣。 常来我们村的炸爆米花的人姓刘,中等身材,黝黑的四方大脸,花白的头发,看上去有50多岁,大家喜欢喊他“老刘”或“刘师傅”。刘师傅用板车拉着小炉子、风箱、爆米锅和一个大麻布口袋。爆米锅中间大两头小,圆鼓鼓、黑乎乎的,极像一颗炸弹,一头有压力表和手摇把,用手轻轻一拨,爆米锅就在铁架上转动起来。 刘师傅进村后,拖着长长的腔调喊几声“爆—玉米花——嘞!”然后,找一处干净的空地,从车上搬下工具。往往他摊子还没支好,就有人端着玉米过来了,后面跟着提着篮子的小孩。刘师傅赶紧生炉子,“吧嗒吧嗒”的风箱将炭火吹得忽明忽暗,不一会火苗旺起来了,装着玉米的爆米锅也开始“咕噜咕噜”地转了起来,玉米粒在锅里面发出“哧啦哧啦”的响声。 约有五六分钟,刘师傅感觉火候到了,看看压力表,起身将爆米锅提起,冲着我们一群小孩儿大喊一声:“捂住耳朵!”我们双手捂耳,眯着眼睛看着他麻利地操作。只见他用麻布口袋的皮圈套住锅盖把柄,放平爆米锅,左脚踩上去,右手拿一个小钢管套住锅盖把柄,使劲一扳,“砰”的一声炸响,白烟冒出。已在爆米锅肚子里闷得难受的玉米粒一下子冲进麻布口袋,膨胀成大个儿的玉米花,像一朵朵金黄灿白的花竞相绽放。 霎时,香味就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向四处溢开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玉米香,能扩散半条街。馋人的香气将孩子们的口水都引了出来,一串串挂在嘴边。 接连的“爆炸”声,陆续召来了很多人。刘师傅的身旁排起了一溜儿盛着玉米的篮子。刘师傅一手拉风箱,一手加炭块,不时拨动一下爆米锅,爆米锅保持着转动状态。有时,刘师傅高兴起来,会唱几句豫剧《卷席筒》。虽然比不上戏班子唱得好听,但他自我陶醉的样子,也让人们投去赞扬的目光。 “呼呼”作响的火焰和“砰砰”的爆炸声,把整个村子都动员起来。孩子们越聚越多,围在爆米花摊子的周围,玩起了各种各样的游戏。“砰”的一声过后,大家的目光马上搜寻喷薄散落在麻布袋外的米花粒,蜂拥而上争抢着,甚至来不及将爆米花上的泥土吹去,便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,争抢的场面既热闹又充满刺激。 也有因争抢引发的吵闹甚至打斗。有一次,我在低头抢玉米花时,头撞着了一个小男孩儿的头,我的头撞得生疼,用手揉了揉,扭头去玩了,而那个男孩却坐在地上“哇哇”哭了起来,说我故意撞他。他的母亲在旁边排队等着爆米花,走过来,不问青红皂白,劈头盖脸对我吵骂起来。 刘师傅放下手头的活计,过来劝解,说:“小孩子抢米花,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,不收你家爆米花的钱了,消消气。”那个小男孩不哭了,他妈也不骂我了。刘师傅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:“男子汉,坚强点,别往心里憋气。”我站在远处,看着刘师傅忙碌而从容的身影,突然很感动,觉得刘师傅是个好人。很多年过去了,那一天的情景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,不时闪现出来,让我懂得了一个朴实的道理:艺品如人品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传统爆米花离我们渐行渐远。街头、商场、影院出现了爆米花的升级版,加工技艺和配方也很考究,有多种口味的爆米花。而我留恋的还是传统的爆米花,留恋的不仅仅是那味道,还有那些乐趣与乡愁。 |
- 上一篇:风雨沧桑西街村 □郝子奇
- 下一篇: 篝纺 □李根柱
豫网版权与免责声明:
1. 本网注明来源为豫网的稿件,版权均属于豫网,未经豫网授权,不得转载、摘编使用。
2. 本网注明“来源:XXX(非豫网)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,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。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,可与本网联系,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。
3. 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等其它问题,请在30日内同本网联系。邮箱:hnshw888@126.com
| >> 发表评论 | 共有0条评论 |